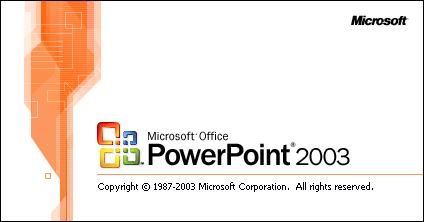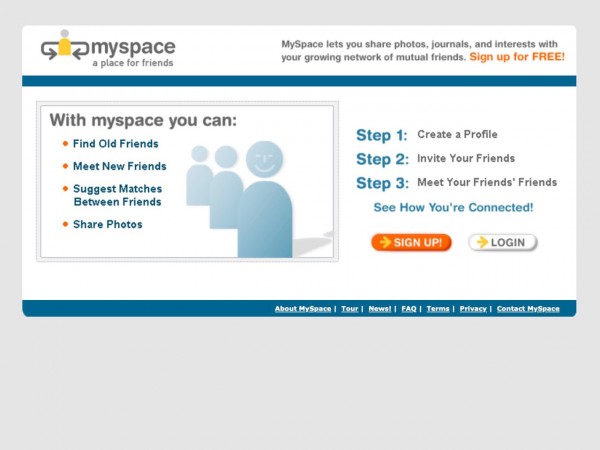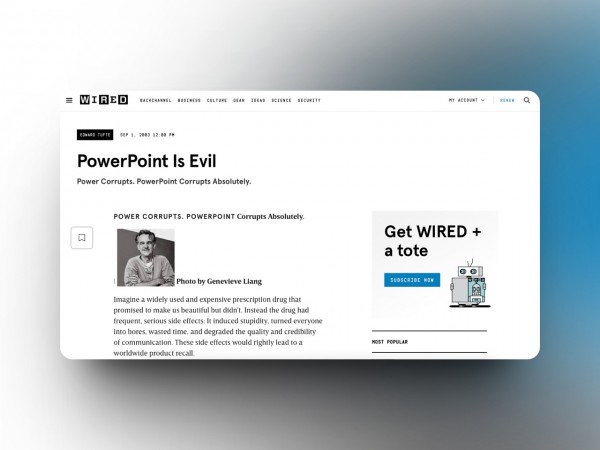2003年的PowerPoint认知大恐慌
这种新媒体技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蠢,正常的人际互动惨遭削减、一切的背后都成了营销。它会腐蚀我们的思想、降低沟通效率、浪费宝贵的时间。正如一位著名艺术家所说,新媒体的兴起正沿着商业、政务和教育迅速传播,预示着“理性的终结”。最终,它甚至可能因为国家电视台在直播中拍下七名美国人死亡的画面而受到指责。没错,这一切发生在2003年——美国民众正对微软PowerPoint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颠覆和风险大感恐慌。
苏格拉底曾经警告说,书面文字会削弱我们的记忆力。文艺复兴时的博学家康拉德·盖斯纳则提醒称,印刷机将把人类的心智淹没在“令人困惑且有害的大量书籍当中”。之后的几代人也面对新技术时不断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广播、电视、电子游戏,这些都号称会腐蚀儿童的大脑。单在过去15年间,人们就曾先后对谷歌、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敲响了警钟。其中一些批语似乎已经过时,但也有一些也在时间的洗礼下得到了验证。而这其中,还隐藏着一种更高层级的技术恐慌。是的,这种恐慌现在已经无人提起,但在当年,人们真心相信PowerPoint——Office套件当中最具表现力的选项,可能代表着能够误导人类、扭曲认知的邪恶力量。
二十年后,这场“幻灯片大恐慌”听起来又滑稽又荒诞,也有一丝悲剧色彩在里面。当时,社交媒体时代已经初现端倪:MySpace和LinkedIn已经成立,Facebook也刚刚亮相几个月时间。但即使抛开那帮“二极管”们的过激言论,我们仍然有必要关注这场涉及生存威胁的大讨论。当时的人们到底是反应过度,还是说这层层荒谬之下其实确有值得反思的成分?
2003年2月1日早上,在距离着陆还有16分钟时,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得克萨斯东部晴朗无云的空中突然解体。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随着航天飞机碎片呼啸着冲向地面,直播观众们见证了这场气势恢宏又残忍惨烈的人造流星雨。
美国航天局(NASA)事故调查委员会随后发布报告,确定引发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是一块绝缘泡沫在升空后不久就松动并损坏了航天飞机的左翼。同时,报告还提出了一个不那么直接、甚至令人难以想象的罪魁祸首。早在哥伦比亚号试图重返大气层之前,工程师们就已经知晓、但却不恰当地低估了机翼损坏的情况。这项分析结论,被掩藏在了他们向宇航局官员展示的一连串晦涩难懂、内容过于繁杂的演示幻灯片中。报告指出:“完全可以理解,当时的高层管理人员为什么看到了这份PowerPoint幻灯片,却没能意识到这个可能危及机组人员生命安全的隐患。”报告随后认为:“这也再次证明,在NASA的技术沟通中大规模使用PowerPoint幻灯片而非技术论文,是存在问题的。”
PowerPoint在当时不是什么新技术,在如今的世界,也早已无处不在。1987年在这款程序首次推出时,销量仅为4万份。十年之后,其销量已经来到400万份。到2000年代初,PowerPoint已经占据演示软件市场95%的份额,并凭借对美国民众说话和思考方式的渗透与影响引发广泛批评。伊恩·帕克(Ian Parker)2001年在《纽约客》上发表专题文章,认为该软件“虽然能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但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如何组织信息、组织多少信息、如何看待世界等。”身为“互联网之父”之一的温顿·瑟夫(Vint Cerf)打趣道:“Power(权力)导致腐败,而PowerPoint导致绝对的腐败。”
到2003年初,“PowerPoint引发死亡”的说法已经成为热门观点。耶鲁大学统计学家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则率先将其纳入严肃讨论。就在2003年春天,塔夫特发表了一篇言辞凶猛的抨击,题为《PowerPoint的认知方式》(The Cognitive Style of PowerPoint),其中包含他对这款软件在哥伦比亚灾难中起到的作用。文章封面是塔夫特自己设计的漫画,内容是一张阅兵照片,一组组方阵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巨型雕像前排成了完美纵队。画中一名士兵说:“没有什么枪毙名单能跟斯大林的相提并论!”另一人则回道:“但为什么总要把幻灯片的内容大声读出来?”这时,连雕像也张口说话了:“请切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篇文章借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即传播媒介会对实际传播的内容产生影响,而PowerPoint作为这样的媒介确实引发了令人困惑、过度简化的效果。它倒不一定会产生含糊、粗糙的表述,反而是把有用信息掩藏在了太多不重要的细节当中,而这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这正是塔夫特在哥伦比亚工程师的幻灯片中看到的情况,他宣称“PowerPoint的认知方式影响了分析结果”,而NASA在几个月后的调查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尽管塔夫特的立场相当激进,但人们还是愿意认真参与讨论。当时的他已经是社会上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信息设计一日游课程与其说是巡回演讲,倒不如说是明星见面会。每场会议都有成百上千人挤进酒店宴会厅。一位作家当时评论道:“他们对于塔夫特演讲的热情,就像是古希腊人去听苏格拉底或者未来的超验主义者讲跨时代的知识一样。”所以当这位“数据界的达芬奇”打算参与这场“PowerPoint大辩论”时,人们自然拭目以待。
《连线》2003年9月摘录了他的文章,标题为《PowerPoint是一种恶》(PowerPoint Is Evil)。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在对年内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想法做回顾时,也选取了塔夫特的评论——总结来讲,就是“PowerPoint会让人变蠢”。其中写道:“也许PowerPoint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混乱无序的现代化时代。”文章甚至提到,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也是用PowerPoint向联合国提交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
认真读下去,我们会在杂志的“罪状”清单中看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条目:社交网络。尽管PowerPoint扭曲美国人认知的“恶行”受到了几乎一边倒的批判,但Friendster、LinkedIn和其他社交网络的作用倒是尚无定论。文章称,也许通过增强社群之间的联络,社交网络能够减轻我们“刻在民族基因中的孤独感”。也许社交网络未来会“进一步将生活割裂成线上、线下两个不同的领域”,或者它们并没有那么强的变革性——至少不能跟PowerPoint这种高度普及且极具影响力的技术相提并论。
如今81岁的塔夫特早已退休。而最终统计数字显示,他的“巡回演讲”共吸引到32万8001名参与者。如今的他主要搞雕塑,但也继续保持着自己的习惯——非常讨厌PowerPoint。他像个小孩一样鄙夷地称其为“PP”并且沾沾自喜。如果大家对之前提到的斯大林漫画感兴趣,也可以在他的网站上以14美元买到一张同款海报。
今年5月,我给塔夫特发了封邮件,询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对PowerPoint的批评已经过时了。一如往常,他专门给我回了一份长达16页的PDF,其中包括他书中言论的摘录还有关于这些书籍的简介。最终,他同意通过电话交流,但我打过去的第一通电话就被转到了语音信箱。他的留言提示也很有个性,“在这片时间已经消失的土地上,我没有空。我们只能用语音信箱,或者短信沟通。说吧!嘟……”
在我最终联系上他时,我问他经过20年的时间验证,PowerPoint是不是真的让人类变蠢了。他回应说:“我也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另一片天地,现在的我是名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是最难沟通的那类人,因为从2003年以来就没人胆敢在他面前展示PowerPoint文稿了。他还宣称自己没有“一直留意”,但最近有消息说,他曾经帮助杰夫·贝索斯禁止亚马逊的高层管理人员使用PowerPoint。
贝索斯肯定不是唯一一个认同塔夫特判断的人。乔布斯也曾经禁止在苹果的某些会议上使用PowerPoint。2010年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前国家安全顾问、时任陆军上将的H. R. 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将PowerPoint描述为一种内部威胁,也曾在作战中禁止使用。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将军也在同一次会议中强调:“PowerPoint让我们变得愚蠢。”2011年,瑞士某前软件工程师组建了反PowerPoint党,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支真正致力于对抗幻灯片暴政的政党。
当然,批评塔夫特文章的声音也不少。有些人指责他为了拉高课程的人气而故意制造争议话题,也有人觉得他搞错了,这是把软件本身跟用户习惯混为一谈。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2009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称:“任何一棍子打死PowerPoint的言论都是愚蠢的。这跟指责讲座没什么区别——在PowerPoint演示文稿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提纲糟糕的讲座、没提纲的讲座,还有幻灯片、小黑板之类。”长期担任麦肯锡商业视觉演示总监的吉恩·泽拉兹尼(Gene Zelazny)则将塔夫特的论点总结为“把司机造成的事故都归咎于汽车”。
这种粗暴比较的问题在于,美国的交通系统确实对当地每年发生的3到4万起车祸死亡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没有私家车自然就不会有这些事故。塔夫特认为,PowerPoint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会促进各种糟糕的演示。“这对演讲者来说倒是方便了,但对观察和内容传播来说不仅不方便,甚至有害。”
但如果说这些糟糕的演讲真的引发了什么广泛的社交弊端,那也实在是没什么真凭实据。有些科学家试图对所谓的PowerPoint效应做点量化研究,想搞清楚这款软件是不是真的影响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瑞士圣加仑大学创意与设计教授塞巴斯蒂安·科恩巴赫(Sebastian Kernbach)与人合著了多篇关于此类文献的综述。他告诉我,总体来讲,研究表明塔夫特的观点算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PowerPoint似乎没有让人变得更蠢,毕竟没有证据表明使用PowerPoint的人出现了信息记忆率降低或者总体认知能力下降问题。但它也确实给信息的传达方式带来了一些强加的影响:更松散、以分条形式表达,并由演讲者灌输给被动接受的听众。科恩巴赫表示,这些习惯甚至重塑了幻灯机时代的环境设计:以往使用幻灯机时研讨会桌往往是圆形的,但PowerPoint时代后则变成了U形,只为了演讲人能走到每个人面前。
在跟科恩巴赫交谈时,他提到正准备向某大型政府组织的员工做一场关于视觉思维方法的演讲。他说他打算使用活动挂图,类似于用一块块有画面的白板拼凑出幻灯片,甚至观众也能参与绘画。但他也准备了比较传统的PowerPoint文稿。他告诉我,这么做是为了向听众证明自己“做了精心准备、足够专业”。这里说的政府组织,就是NASA。
其实NASA仍在使用PowerPoint这事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尽管曾经引起媒体的强烈反对、激起了亿万富豪的愤怒,甚至在军队内拉响了红色警报,但这种演示形式仍然盛行。微软PowerPoint产品副总裁肖恩·维拉隆(Shawn Villaron)就表示,该产品的月度用户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目前已达数亿之巨。要说有什么变化,就是如今的PowerPoint更灵活、用例更多样。新冠疫情封控期间,人们甚至在Zoom上举办PowerPoint联欢活动。现在,当孩子们想养只小狗、退出球队或者参与明星见面会时,都会做份PowerPoint向父母解释自己的理由。如果PowerPoint真是种恶,那邪恶已经统治了整个人类世界。
至少从表面上看,PowerPoint会让人变蠢的说法就像是教科书上那些误导性的技术末日论案例。在要求塔夫特重新审视自己的批评时,他明确表示反对。但在后来的谈话中,我还是当面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这项新技术的批评是否可能有失偏颇?毕竟很多人都会做出这种错误预判。之前人们对印刷机或文字处理器都有过类似的抨击,那他对PwerPoint的断言有什么不同吗?
但还没等我彻底说完,他就打断了对话。他明显愤怒地表示,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我不搞那些宏观讨论、说些假大空的废话。我自己就在前线,一刻也没停止过沟通。”根据我的理解,他可能是想说自己不参与任何遥远、抽象的历史性思考。
我又尝试缩小了问题范围。我说,目前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担忧跟当初PowerPoint面临的批评有一定相似之处。两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担忧,即新媒体技术更重视形式、而非内容,其设计目标在于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非传达真理,这恐怕会让人变得更蠢。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塔夫特的批评其实是正确的,只是矛头指向的技术对象错了。他仍然否认,并表示拿PowerPoint跟社交媒体比较属于“胡说八道加乱押宝、扮先知”。
尽管塔夫特非常不配合,但我还是非常好奇,如果包括他在内的评论家们能在2003年就敏锐嗅到社交媒体的深远影响,那事态究竟会如何发展。也许当《Friendster的认知方式》或者“LinkedIn是一种恶”登上《连线》杂志的头条,真的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如果当初对社交媒体的警惕和抵制能一直存在,那Facebook也许不会成长为现在这样的庞然大物,美国社会也不会变得如此割裂。
或者,现实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无论有没有把握住那个时间节点,也无论评论家们多么有预见性,对于新媒体的担忧似乎都很少产生实际影响。反对意见总是遭到压制,新技术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多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过去并认为当初的担忧纯属无稽之谈,那可能是因为这项技术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把我们成功同化了。
书面文字毁掉人类的记忆力了吗?广播是不是让我们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PowerPoint是不是把我们变成了没有自主思维的行尸走肉?如果说这些创新确实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那我们就只能用改变之后的思维来衡量其影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批评到底是对是错将永远无法区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
来源:The Atlantic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
AI智能体漏洞挖掘成本骤降,Anthropic呼吁AI防御
Anthropic发布SCONE-bench智能合约漏洞利用基准测试,评估AI代理发现和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缺陷的能力。研究显示Claude Opus 4.5等模型可从漏洞中获得460万美元收益。测试2849个合约仅需3476美元成本,发现两个零日漏洞并创造3694美元利润。研究表明AI代理利用安全漏洞的能力快速提升,每1.3个月翻倍增长,强调需要主动采用AI防御技术应对AI攻击威胁。
NVIDIA联手多所高校推出SpaceTools:AI机器人有了“火眼金睛“和“妙手回春“
NVIDIA联合多所高校开发的SpaceTools系统通过双重交互强化学习方法,让AI学会协调使用多种视觉工具进行复杂空间推理。该系统在空间理解基准测试中达到最先进性能,并在真实机器人操作中实现86%成功率,代表了AI从单一功能向工具协调专家的重要转变,为未来更智能实用的AI助手奠定基础。
Spotify年度盘点2025首次推出多人互动功能“盘点派对“
Spotify年度总结功能回归,在去年AI播客功能遭遇批评后,今年重新专注于用户数据深度分析。新版本引入近十项新功能,包括首个实时多人互动体验"Wrapped Party",最多可邀请9位好友比较听歌数据。此外还新增热门歌曲播放次数显示、互动歌曲测验、听歌年龄分析和听歌俱乐部等功能,让年度总结更具互动性和个性化体验。
机器人学会“三思而后行“:中科院团队让AI机器人告别行动失误
这项研究解决了现代智能机器人面临的"行动不稳定"问题,开发出名为TACO的决策优化系统。该系统让机器人在执行任务前生成多个候选方案,然后通过伪计数估计器选择最可靠的行动,就像为机器人配备智能顾问。实验显示,真实环境中机器人成功率平均提升16%,且系统可即插即用无需重新训练,为机器人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AI测试成数智化合规必选项,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AI智能体漏洞挖掘成本骤降,Anthropic呼吁AI防御
Spotify年度盘点2025首次推出多人互动功能"盘点派对"
英国SAP用户因商业套件重启授权迷局感到困惑
AWS发布Graviton5定制CPU,为云工作负载带来强劲性能
美光放弃Crucial品牌:告别消费级存储市场
手机里的NPU越来越强,为什么AI体验还在原地踏步?
如何使用现有基础设施让数据做好AI准备
IT领导者快问快答:思科光网络公司首席数字信息官Craig Williams分享AI转型经验
Anthropic CEO警告AI行业泡沫化,批评"YOLO"式投资
雅虎利用AI实时总结橄榄球比赛精彩内容
押注AI智能体,奇奇科技跨越十年的“换挡”与远航